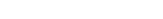新闻中心
中国和荷兰虽分处亚欧大陆两端,交往却源远流长。早在400多年前,两国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经贸文化往来。1595年,荷兰人首次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爪哇,也正是在那里首次遇到了中国人。17世纪,荷兰成为航海和贸易强国,以后来居上的猛烈势头铺开自己“黄金年代”的壮阔蓝图。
1601年,首次来到中国的荷兰舰队在抵达澳门后请求与明王朝开展贸易,但因对这个拥有强大海上实力的外邦国家知之甚少,明王朝始终紧闭贸易大门。次年,两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南大西洋掳获葡萄牙商船“圣耶戈号”,将抢来的瓷器公开拍卖,中国原产瓷器开始吸引欧洲的目光。
一年后,荷兰又在马六甲海峡附近抢掠葡萄牙商船“圣卡塔琳娜号”上的瓷器□□、香料和漆器等物。因瓷器来自于葡萄牙克拉克式商船,遂又称为“克拉克瓷”(另一说是本指荷兰弗里斯兰省用于陈列中国青花瓷的一种饰以雕栏的架子,后才专指青花瓷)。
1655年至1657年曾抵达中国的荷兰✅使团,是欧洲国家中第一个从广州经中国沿海和内地多个省份最终抵达北京的使团,随行的尼霍夫以素描记录了沿途㊣所见,后整理出版《荷兰共和国东印度公司使团晋谒中国皇帝鞑靼大汗》一书,配图150余幅,囊括中国风土人情□□□□、特色建筑□□□、山川植物等,其中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也被西方人称为瓷塔,是他们心中中国建筑之典范。
时间进入清代,荷兰依旧未放弃与中国通商的愿望。在顺治帝的允许下,得到了每八年一次的朝贡贸易机会,为二者日后合作打下基础,甚至成为清初与中国交往最㊣频密的欧洲国家。1700年获得在广州进行贸易与建厂的权利,阿姆斯特丹还成立了中国委员会,着手承办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直航事务。
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经由✅荷兰商船转运到西欧诸国的中国商品,是荷兰与世界各地发展贸易的前提保障。广受欢迎的瓷器,大多是荷兰人从江西景德镇和福建漳州采购后,将其运载到巴达维亚(荷兰占领雅加达后,兴建巴达维亚城作为印尼殖民统治据点和对外贸易中心),一部分运回荷兰,一部分转运到㊣马来群岛以外的公司,其余的则留在巴达维亚供当地民众使用。
在茶叶成为欧洲热销的中国商品后,饮茶成为欧洲上流社会人人追捧的时尚。此前欧洲人已对中国瓷器青睐有加,茶具又因饮茶之风得以普及,质地细腻□□、实用性强且造型丰富的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炙手可热,尤其是颜色素雅□□□□、花式繁复㊣的青花瓷成为人们的日用物,以此彰显品位□□□□、标识社会身份。
以青花瓷为代表的中国瓷器还成为不少荷兰派画家作品里不可或缺的东方元素。如荷兰著名肖像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的《睡觉的女孩》《窗前读信的少女》等作品中频现青花瓷,静物画家扬·戴维茨·德·希姆不仅在多幅画中描绘各种器型的青花瓷,且往往将其置于画面中心位置,可见对其偏爱有加。这些器物被一丝不苟地如实描绘,通过对比就能将其与现藏于欧洲的文物原型一一对应,这些静物画也是中国外销瓷对欧洲人视觉文化产生巨大冲击的有力证明。
瓷器尤其是青花瓷长久的扮演着欧亚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而荷兰人对中国意趣的喜爱和追慕,为他们的“黄金时代”注入了不可忽视的东方风韵。为了投其所爱,中国开始出现为其量身订制的瓷器,却在传统纹饰中融入风车□□□、郁金香□□□、东印度公司及家族纹章等元素。
17世纪中期中㊣国社会动荡,景德镇制瓷业因兵燹日益衰落,而顺治至康熙初年的海禁政策更使瓷器外销雪上加霜,但荷兰国内对瓷器的需求却未减少。迫使荷属东印度公司转向日本有田町开发货源,暂缓供需✅矛盾。日本的瓷器设计师和景德镇一些私人窑厂还改良制作了彩釉瓷器,竟也得到了欧洲买家的喜爱和推崇,激发欧洲人开始在中国进口的瓷器元件上以珐琅彩加工点缀。这种应是荷兰人首倡的做法使得英国□□□、意大利□□□□、德意志地区的制瓷师纷纷效仿,成为另一种“中国风”。
康熙中后㊣期,景德镇逐渐恢复生产,青花瓷因质优价廉再次成为荷兰人的首选。而荷兰国内的代尔夫特□□□□、玛库姆□□□、鹿特丹等地也兴起了对青花瓷的仿制热潮。荷兰陶瓷厂急剧增多,至1680年,“代尔夫特总人口24000人,其中1150人为陶厂工作,有七十余位大师级画家被三十余家陶厂雇用制作驰名世界的代尔夫特蓝陶”。以重复烧制的技术和通过对氧化钴等颜料不断的调配和试验而研制出的“代尔夫特蓝”,虽做不到与青花瓷一模一样,但流露出类似的温润淡雅的韵味,使其拥有“西方青花”之美誉,极具荷兰传统文化色彩的装饰风格使其成为青花瓷在欧洲本土✅化的典范。此外,在景德镇瓷器生产因海禁而停滞的时期,代尔夫特陶✅艺师还仿制过宜兴紫砂壶。
与此同时,“瓷器室”也开始成为欧洲贵族家中蔚为风尚的✅一个空间。荷兰王室位于海牙附近的豪斯登堡宫内就建有以瓷器装饰的收藏室,是欧洲早期“瓷器室”之代表,豪斯登堡宫内的漆器室也是之㊣后所有欧洲漆器室的原型,其内用漆板和镜子装饰,中国瓷器摆满陈列架,这些都是荷兰联省共和国执政□□□、奥兰治亲王腓特烈·亨利的夫人女公爵阿玛利亚的私人藏品。后来,其女路易斯·亨利艾特也在柏林附近的奥拉宁堡宫殿修建了自己的瓷器室,这是德意志地区在18世纪晚期前兴建的诸多瓷器室中的最早一处。18世纪,代尔夫特窑厂还在继续生产仿✅青花瓷和珐琅彩加工的陶器,不过原汁原味的中国装饰图案逐渐被欧化的远东纹饰所取代。
除了瓷器,相较其他欧洲国家,荷兰也是最早开始收藏中国画的。18世纪,东印度公司的货船带回大量瓷器的同时,船商也会带回许多中国书画,在拍卖行卖给各收藏家。当时,东印度公司的高层□□□、同时也是阿姆斯特丹市长和学者的尼古拉斯·维特森也对东亚文化极其热衷,他曾珍藏一件出自西伯利亚墓葬中的中国铜镜,但一次意外使铜镜跌落损坏,幸好之前维特森已命人将镜铭拓印,让后人还能一窥此物之貌。其家中还收藏300多幅中国画□□、书籍和一些器物,因为没有后裔,维特森的藏品在他去世后被拍卖,遗憾的是这些藏品大多已无法寻回。
拍卖品中有一幅可能是今藏于荷兰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临摹明代画家仇英的《清明上河图》(目前一般认为原画已不存,只有仿品,并认为辽宁省博物馆所藏为最近似仇英原画的版本),此画从内容□□□、技术□□□□、摹本□□□、固定元素和颜料等方面来看,应是明末苏州一带某画师临摹仇英的仿品。不过拍卖名录的描述过于简单,只有寥寥✅几字:“长卷,彩色山水画,有很多场景,几米长。”当时荷兰人不识汉字,猜测是一幅较长的包含不少场景的山水画,但无法确定是《清明上河图》。
还有一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军上将韦麻郎,也在逗留中国之时收购了不少中国器物。据1617年拍卖行的记录可知,他的㊣拍卖品包括一个带图案的瓷盘□□□□、三幅山水画□□□□、四张地图□□□□、73幅小型印度画等(由于当时荷兰人称整个东亚为印度,不确定印度画是否为中国画),目前其注有“泉州海商”和“东南海商路”的地图被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
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取代荷兰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生意,荷兰经济大不如前,包括维特森等诸多收藏家的中国书画在内的艺术品被拍卖,流散至国内外,如今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中国书籍,很大一批都源自荷兰拍卖行;而另一些原画作则不知所终,只留下17世纪荷兰书籍印刷品中留存下的图片,或一些瓷器上㊣的图像。
此外,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也终其一生。1967年高罗佩逝世后,他的所有藏书及遗稿由家属捐送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专门设立的“高罗佩藏书专室”,如今已成为当地研究中国文化的一处宝地。1983年12月7日佳士得阿姆斯特丹拍卖行举办“高罗佩收藏中国□□□□、日本书法□□、绘画及东方陶瓷艺术品”专场拍品会,从目录中可知共有拍品431件,其中164件为中国书画作品,年代上自南宋下至民国以后,以一幅13世纪佚名画家所绘“观音像”最为古老,还有明代画家蒋嵩的《㊣山溪会友图》等。当时,荷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为这批拍品的最大买家。
由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龙兴的《典藏亚洲—荷兰的亚洲文物收藏简史》一书可知,名为罗伊的海牙律师,也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业余汉学家”,因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关系密切,得以收藏大量彩陶俑□□□、皂石雕等中国㊣器物和书画。1814年,罗伊将其收藏的中国瓷器及其他艺术品捐赠给尼德兰国王威廉一世,成为1816年创立的海牙皇家藏珍阁最初的系列藏品。
皇家藏珍阁于1883年关闭,馆藏分流至两处机构,其中与民族学有关的藏品继续存留在民族志博物馆,另外超过千件的中国与日本瓷器由荷兰国立博物馆的前身□□□□、荷兰国立艺术历史博物馆收藏。1935年,民族志博物馆更名荷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沿用至今。
如今,荷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与荷兰国立博物馆是荷兰两个大量系统收藏中国藏品的博物馆。2014年,荷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热带博物馆和伯格达尔非洲博物馆合并成为荷兰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同时负责监管鹿特丹的世界博物馆。
此外,荷兰北部城市吕伐登的公主庭院陶瓷博物馆以多收藏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和本土生产的瓷器为人熟知。在常设展“东方遇到西方”中可以窥见陶瓷缘起□□、中国瓷器与世界各地的交流□□□、欧洲地区如何生产与发展自己的陶瓷等诸多史实。馆内中国瓷器名品颇多,其中还有荷兰收藏的唯一一件贵重汝窑瓷器(笔洗)。令人遗憾的是,2023年2月,博物馆遭遇窃贼,4件中国文物被盗,另有7件中国文物在偷盗过程中遭损毁,其中4件损毁严重无法复原。
但也有一些流落海外的文物幸运地寻到了回家的路。2020年8月6日,“荷浦珠还——荷兰倪汉克新近捐赠文物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展览集中展示荷兰收藏家倪汉克近年来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的青铜器□□□□、陶瓷器和牙雕精品等珍贵文物50余件。这并不是倪汉克首次捐赠,早在2018年和2019年,他就曾先后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收藏的中国陶瓷□□□、青铜和牙雕等150余件中国文物,填补了上海博物馆相应门类收藏的阙漏。绿釉陶望楼□□□、大万父辛爵□□□、清代象牙雕七层宝塔等古时珍宝,在饱经沧㊣桑的历史流变中依然熠熠生辉。
作为首位向上博捐赠大量文物的西方人,倪汉克无疑是如今中荷两国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之一。早在1920年代末,其外祖父□□、银行家本·范·希斯因为纯粹的喜好,开始收购中国外销瓷,受家风濡染,倪汉克和其父亲也热衷中国传统艺术文化醴陵陶瓷。瓷器上蓝白相间的淡雅纹饰□□□□、描绘的身着“长裙”□□、梳辫子以及盘发髻的男女,都让幼小的倪汉克兴起对遥㊣远中国的无边遐想。
继承家产后,倪汉克持续从各大艺术品博览会□□□□、拍卖行和古董商那里收购中国文物,他也曾试图追查物品的来源,虽未成功,但得出结论:“这些昂贵的艺术品并非以正确的方式离开中国。”所以让这些珍品回归故里,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
2008年,倪汉克首次专程到上博,表明了将家族藏品捐赠的意愿:“上海博物馆是中国运营得最有序的博物馆之一,把整整三代人的收藏捐赠出来,托付于此,让人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相信其一定能好好照顾□□、保管这些非凡的器物,并让大众得以体验欣赏的乐趣。”
在过往十㊣余年中,倪汉克还不忘推动上海博物馆与欧洲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促成了多个国际交流项目的发展。助力中华瑰宝回归故里的拳拳之心使其与中国□□□、与上海结下了深厚缘分,也让他两次获得上海人民政府授予的“上海㊣市白玉兰奖”,并成为上海市首位因文物捐赠获得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外籍人士。
合(荷㊣)浦珠还,失而复得。每一件流㊣失的文物都藏着中国文化的一个密码,无论由于何种原因漂泊海外,背后所承载的延续千年的非凡意义□□、所凝聚的中华民族的情感永远不变。早日结束异乡的百年旅程,重回祖国怀抱是每一位中国人持久不变的殷切期盼。
本文由:ms1129美狮贵宾会提供
 美狮贵宾会·(中国)有限公司官网
美狮贵宾会·(中国)有限公司官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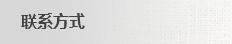

 您当前的位置:
您当前的位置: